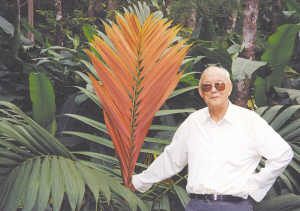冶金工业史
| 【口述史】周传典忆鞍钢往事 |
| 2012-07-03 14:22 |
|
1949年7月4日。鞍钢与整个国家同样面临新生。西北工学院毕业的一位大学生,被“一个命令调到鞍山”,他的成长,从此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联。 他,叫周传典。 对于本刊从鞍山发至北京的问候与采访请求,周传典欣然接受。这位87岁的老人,对那段日子,对鞍钢,对鞍山,所有的记忆依然年轻。 只有“土高炉”,没有“洋高炉” 上周三,一番周折,终于辗转得到周传典的电话。手里是鞍钢党委宣传部提供的周传典简介:周传典,安徽凤台人,1921年生。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鞍钢工作。历任炼铁厂技术员、工程师、值班工长、副厂长等职。1958年调任武钢炼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武钢技术处处长。1964年调回鞍钢任炼铁厂厂长。1965年调冶金工业部工作,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1986年后离休。 捏着人物简历和采访提纲,心下却踌躇起来:且不论老先生是否会拒人千里,仅就一位87岁的老人而言,一段未曾预约的时间不短的采访是否叨扰了老人的清静?仅一通电话,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诚意、渴望甚至身份? 他有太足够的理由拒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鞍山日报》啊?那是我的老关系了!”浓浓的安徽腔,笑着说的第一句话,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 话题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周传典初到鞍钢开始。 “那是1949年7月4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前一年刚大学毕业的周传典正在华东解放区,忽然接到紧急命令,调到鞍山,支援鞍钢建设。“那时候刚解放啊,没有技术人才,日本人在技术岗位上不用中国人,只有在劳动岗位上才用中国人。”技术掌握在人家手中,要开工的鞍钢极度缺乏技术人才。周传典受命于危难之时,2号高炉的生产迫在眉睫。 在有过留学前苏联经历的周传典眼中,当时的鞍钢与前苏联的钢厂根本无法比,“到了鞍钢,高炉、平炉就没见过,几个地方有‘土高炉’,没有‘洋高炉’,当时钢铁生产基本上寥寥无几。”
冶金专业出身的周传典在炼铁厂当上了见习技术员,2号高炉开炉生产,周传典亲眼见证亲身参与。“7月4号是鞍钢的重大节日啊,那天开始恢复生产了。” 周传典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终结了鞍钢“炉内炉外掌握技术的没有中国人”的历史。 日本、美国都没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1950年,2号高炉炉长周传典突破了一项久未解决的技术难题,让世界“傻了眼”。 “当时的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王鹤寿提倡‘矛盾论’,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就靠这个,我们搞了技术创新。”周传典细致地为我讲解这项伟大的创新前后经过:原料的含硅量高,就不适于炼铁。鞍钢原有的9部平炉,有三座用于原料冶炼前的“脱硅”,再到平炉去炼钢。周传典经过研究,在鞍钢2号高炉试用烧结矿冶炼低硅铁获得成功。“当时全世界(原料含硅量)都是1以上,我们把含硅量降到了0.5—0.6,可以直接炼钢了。”由此,把鞍钢三座平炉炼钢变成了9座。 这曾是美国、日本许多年来未能解决的老问题。这个成功,使当时鞍钢炼钢生产能力提高了50%。周传典也因此在1952年被评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并荣立鞍钢复产特等功。 1953年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题为《鞍山钢铁公司是怎样大量培养工人技术员的》报道文章。编者按中提到,“鞍山钢铁公司用速成办法把大批工人培养成技术员,这种作法简单易行,很有成效,全国任何一个大、小厂矿都可仿效。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像鞍钢这样,利用现场当课堂,请技术人员作老师,加速培养技术人才,就可以大大增强我国工业建设的力量。” 文中举例“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过去教工人李凤恩的时候,每天八小时,两个人在一起形影不离。周传典谈他教李凤恩看高炉风口,“每次总是让他先看,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我看,批评他的意见,最后再让他看……”这样曾反复进行过很多次。教李凤恩看铁样,抄化验表,也都是这样。周传典就在这些操作过程中,给李凤恩讲“氧化”、“还原”的道理及一般的化学、物理知识,并写过很多讲义。 周传典与李凤恩结成了互帮互教对象,曾被评选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佳典型。采访中,记者提及李凤恩,周传典不提自己的“为师之道”,却对这个“学生”赞赏有加:“(李凤恩)人比较聪明。我担任炉长时,他成了学习高炉技术的技术员;我当值班长、厂长时,他就是工长了……” 周传典先后两次在鞍钢工作,累加起来逾十年。从一个见习技术员直到厂长,甚至官至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的成长、成熟是在鞍钢,对这里他始终有份与有荣焉的认同感。 正是因为奉行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鞍钢的技术力量一下子异军突起。“全国当时只有鞍钢这一个现代化的钢厂,有一万五千名技术人员,后来都调到各个省,开辟全国各大钢铁厂。”周传典本人也在1958年被调到武钢工作。回忆至此,周传典做了个好玩儿的比喻:“鞍钢是个老母鸡,下蛋下到全国!”“全国(钢铁)技术从哪里来?从鞍钢来!” 1964年,周传典再次被“点名”调回鞍钢炼铁厂任厂长,这是再一次的受命于危难之间。 毛主席睡不着觉了 周传典与鞍钢之缘,总有那么点儿患难真情的意味。 第一次来鞍钢,正式开工;第二次回鞍钢,面对的是“大跃进”后的凋敝。1964年,由于鞍钢有8座停产的高炉要恢复生产,周传典被再次调回鞍钢任炼铁厂厂长。 “大跃进就是大破坏!”周传典说,1956年鞍钢的生产指标超过了日本和前苏联,而一场“大跃进”,又让鞍钢退回到破烂不堪的惨状。“那几年大刀阔斧整改,到1966年,鞍钢又创造了新纪录,生产指标再次超过日本、前苏联……” 1965年,出了件“让毛主席睡不着觉”的事。这事,再次需要周传典离开鞍钢。 早在1958年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批转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报告。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要加快“大三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并请周总理主管这件事。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刘彬约周传典谈话说:“国家决定建设西南三线基地,而攀枝花钒钛铁矿冶炼是一个世界性的特殊难题,如果钛铁分离技术关攻不破,大钢铁厂就不能建设,机械军工工业也搞不起来,打起仗来怎么办?毛主席因此睡不好觉,决心组织试验,国家决定抽调你去。”解决攀枝花铁矿的冶炼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于是他火速赴京。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在与他谈话时说:“一旦打起来,沿海是靠不住的,武汉、包头、太原的钢铁厂也在敌人的轰炸圈内,现有的钢铁厂大都不能生产了,没有钢铁打什么仗?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乌拉尔建了几个大钢铁厂。卫国战争中,乌拉尔以西的钢铁厂被德国人占领、破坏了,而苏联就是依靠乌拉尔的这些钢铁厂打败了希特勒。所以,中央已经决定在攀枝花建设后方战略基地。西南地区除钒钛铁矿资源足以建设大钢铁厂外,再没有什么大的矿藏了。”
(本文选自2008年9月3日《壹周刊》) |
| 编辑: 张明 来源: | |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三区26楼 邮编:100029 电话:(010)64453751 传真:(010)64410636 电子邮箱:csteelnews@126.com 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法律顾问:大成律师事务所 杨贵生律师 电话:010-58137252 13501065895 Email:guisheng.yang@dachenglaw.com 中国钢铁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京ICP备07016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