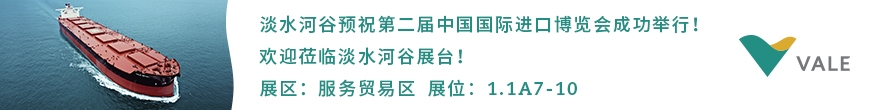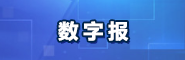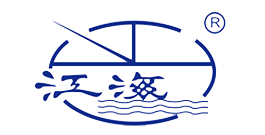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呼吁采取货币与财政政策同时刺激的声音重新抬头,其中一个观点是,必须尽快实行扩张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必要过于顾忌财政赤字率的3%门槛。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通过扩张性政策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因为,一旦经济减速,“将会使结构性改革、制度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面临困难,经济稳定,金融稳定,甚至社会稳定将难以保持”。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历史经验指导下,中国经济也陷入过于频繁的调整怪圈:经济冷了就刺激,经济刺激后就过热,进而不得不加以抑制,抑制又产生冷却效应,然后不断循环。
不得不说,这导致经济增长对政府干预越来越依赖,也不断缩短周期,实体经济自身的市场机制一定程度被扭曲,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庞大的债务规模以及投资效益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中国自十八大来推动经济改革的原因之一。
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终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是改革的主要路径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稳中求进与兜底思维,但改革不应该动摇。改革的核心理念是重视增长的质量而非速度和规模。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有必要采取稳定的措施,财政政策确实应该更积极,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减税降费、扩大民生支出以及在农村、城市群等基建领域补短板。这既要求尽量减少一般性财政支出,同时意味着应该需要提高赤字率。
但是,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也是有限的。经济发展,既要看分子,也就是注意债务,还要看分母,也就是经济增长。一般而言只要经济增长,债务就会被稀释。但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往往需要维持较低的利率,这就是降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本,但是这就会带来通胀的压力,目前人民银行货币扩张空间到底多大?这是需要一个谨慎对待的问题。
通过增加政府债务以及信用扩张维持增长,的确可以促进增长,做大分母。但政府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大幅投资基建的做法会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扩大投资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资源会一定程度上流向低效率的部门配置,比如钢筋、水泥、煤炭等领域,从而大幅增加其他部门的成本。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资产炒作与投机,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得增长质量与效率下降,但成本又过高,放大经济增长风险。
其次,持续依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增长会产生一个并不明显但会长期积累的风险,即全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低息的政策一般对政府、持有资产者以及能够轻易获得信贷资源的人更有利,比如国企、炒房者等。对一般群体很不利,因为他们会为持续宽松带来的通胀或资产泡沫埋单,但没有公平地享受增长收益。
分配不公与现实通胀导致大部分中低收入者难以增加消费,进而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中国的房产泡沫已经抑制了社会消费,也就阻碍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
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产生了基于房产泡沫的次贷危机,然后几轮量化宽松政策扩大了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必须避免分配不公带来难以控制的社会挑战,经济政策应该更普惠和公平。
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人口拐点已经显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之前,中国需要尽快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即依赖技术驱动,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继续重视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一旦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没有实现创新驱动,意味着过高的债务、过高的抚养比以及过低的增长形成双重压力。
目前,中国的债务依然在安全范围内,经济的韧性与空间均在。我们处于转型过程中,转型意味着旧体系遭受破坏,新体系在建设过程中,旧事物被淘汰会让市场运行、观念、预期同时受到冲击,容易产生一些悲观情绪,需要预期管理。但是,预期管理不应该用“保增长”的方式进行,因为刺激本身可能带来的收益不足以覆盖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