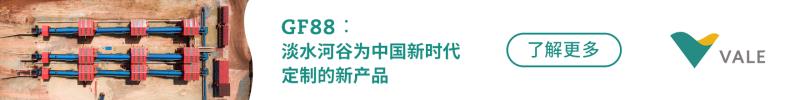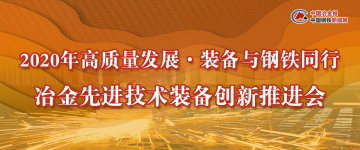本报记者 吴兆军 通讯员 贾泽昊
面对1500摄氏度以上的钢水,他用手套遮住刺眼的光线,快速拿起取样器,取出一个钢样。虽然他这一系列动作都很娴熟,但是汗水早已浸透了工装——这,就是河钢邯钢一炼钢厂共产党员、青年炼钢工唐旭阳的一个平凡的工作场景。从炉前工做起的他,仅用3年多时间就熟练掌握了炼钢技能。
要当最好的炼钢工
“我爷爷从事炼铁工作,父亲也是先到炼铁厂后到工会工作,当我小时候看到熊熊炉火时,就喜欢上了冶炼,决心长大后要当个炼钢工,来报效邯钢。”唐旭阳说。
2015年,唐旭阳大学毕业后来到河钢邯钢一炼钢厂。“我要努力学习技能,当最好的炼钢工。”唐旭阳信心满满,要把夙愿变成现实。
“炼钢工是一个技术活儿,没有六七年的操作实践和技术积累,很难得心应手。”唐旭阳的师傅王嘉斌介绍。
自此之后,转炉前、炉火旁、操作室就成了唐旭阳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在这一批年轻人中,旭阳是‘事’最多的一个,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问个不停,直到弄懂了才罢休。” 王嘉斌笑着说。
在一次冶炼过程中,检测钢水成分的副枪发生故障,不能检测冶炼终点成分,这让唐旭阳慌了神,“没有副枪,就好比打枪没了靶子,心里没有底啊。”
唐旭阳急忙请教一旁的师傅,师傅说:“其实我学炼钢的时候都是通过观察火焰来判断温度和成分的,副枪自动检测成分是好,但要学会用肉眼判断一炉钢炼成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好炼钢工。”
唐旭阳牢记这句话,学着用肉眼判断温度和成分参数,很用心地在小本子上记下各个钢种的特征和对应火焰。经过数千次的悉心观察,他练就了一双看钢水温度的“火眼金睛”。
8月7日,3号转炉前,通红的钢水把唐旭阳胸前的党徽映照得闪闪发光。“这炉钢的温度感觉有1590摄氏度。”他在对讲机里问。
“测温器显示1593摄氏度。小唐,你看钢水温度的眼力差不多了。”师傅在对讲机里欣喜地回答。
关键时刻顶得上
今年初以来,河钢邯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倾力生产百米重轨高端产品,服务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复工复产用钢单位的增加,河钢邯钢重轨钢的订单逐渐增多。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满足客户需求,成为该公司关注的重点。为了确保百米高速轨和重轨的钢水高质量,唐旭阳暗暗地与高质量钢水较上了劲。
8月13日,一批高速轨订单的钢水冶炼正在紧张进行。“对于炼钢来说,加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选择正确的时机,才能把成分控制在完美的区间内。”唐旭阳介绍说。
冶炼U75V重轨钢,唐旭阳在对讲机内通知操枪工加合金料时,发现加入的炼钢原料结成了坨。“结坨的合金料会影响吸收率,有可能造成成分误判乃至降级。”
经过短时间的思考后,他想到了让重轨产品指标再提升的方法:快速统计加料数据,以秒为单位估算可以调整的区间,从而保证钢水成分的稳定。
在以后冶炼钢轨产品时,唐旭阳不断摸索调整加料顺序和加料量,探索出了一套针对重轨钢冶炼的最佳加料模型,为下道轧制工序提供了良好的铸坯原料。
“知道我们生产的2万多吨350千米/小时百米高速轨用到国家铁路工程——鲁南高铁时,一种钢铁工人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唐旭阳说。
精细化操作流程要丝毫不差
唐旭阳的座右铭是:一心让精品钢轨铺设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为保证产品质量,他有时会因为一些操作细节和老师傅们“争吵”起来。
“不行,必须执行精细化操作流程,差一点儿都不行!”日前,在生产调度室内,唐旭阳和值班长起了争执。
原来,重轨钢的冶炼准备环节十分严谨,钢包还没有烘烤至规定温度,值班长就急着按列车时刻表开始组织生产。
“我炼的钢最后是要承载生命安全的,生产环节哪一个不符合标准,这钢我都不能炼!”唐旭阳倔强地说。
1月~7月份,唐旭阳带领班组冶炼的重轨钢终点拉碳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温度合格率在98%以上、产品一次合格率均超九成。
《中国冶金报》(2020年09月04日 03版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