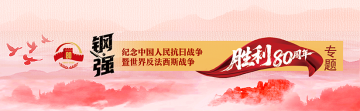何立胜 杨志强
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提出:“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做强国内大循环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或潜力为基础,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大国经济须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
大国经济的特征是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笔者认为,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性在于4方面。首先,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既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又是稳定经济发展的治本之策。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4.5%,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9%,相比于2010年的历史低点(34.6%)提高了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但从横向比较看,依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其次,从投资结构看,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中期,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推进碳中和,提升产业技术升级等投资空间广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投资潜力巨大。再次,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看,做强国内大循环,可以充分释放消费、投资需求,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强经济韧性,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后,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来看,长期以来,中国投资与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全方位扩大内需正是对这一结构性失衡的修正。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到经济稳定,又关系到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从实际作用的角度看,做强国内大循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历史经验显示,在外需波动较大(如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而内需(尤其是消费)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时,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有利于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又有助于改善和塑造我国的地缘经济与贸易环境。
其次,全方位扩大内需可破解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堵点”。当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集中在供需错配、交易效率低等方面,需通过需求升级(如绿色、智能、高端产品的需求)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破解供需错配;通过“流通革命”(如电商下沉、冷链物流、供应链金融)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流通效率。
最后,有利于增强国际竞合新优势。国内市场越强、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
有效释放内需潜力,畅通大循环是理性选择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困难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消费增速放缓和物价疲弱则是表象。做强国内大循环,短期要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则要围绕全方位扩大内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把增加收入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影响消费的因素较多,而收入是首要、就业是前提、社保是基础。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一致。
此外,社保保障水平不高、公共服务发展不充分也影响了消费。民众对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有着旺盛的需求,要加快向民营资本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性行业。
二是优化供给质量,让供给更好匹配需求升级。供给优化不是简单的“生产更多产品”,而是让供给能力与需求升级同频共振。一方面,传统产业实现向高端跃升,如纺织业从“低端代工”转向“功能性面料(抗菌、防晒)”提升附加值;钢铁业从普钢转向特种钢(新能源汽车用硅钢)。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实现“扩容增效”,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卫星互联网、人形机器人等,填补高端供给缺口;服务业实现“提质扩容”,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设计、金融科技)和生活性服务业(医疗康养)向专业化、高品质转型,在扩大商品消费的同时,推动服务消费扩容。为此,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新型科技企业发展。
三是统筹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效。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必须保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的动态平衡,持续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效。若经济循环畅通,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将持续增加,实现供需有效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将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过程;反之,则会影响经济运行的质效。统筹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四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体制基础。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消除在市场准入方面遇到的障碍,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
五是做强国内大循环决不是封闭运行,而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重点是在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国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国际对接,核心是“边境后”规则的国际对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泛且错综复杂,要综合考量,实现制度型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结合,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为平台持续打造制度型开放试验田,与高标准国际通行规则相容相通,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何立胜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杨志强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均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